进山中学的抗日壮歌
进山中学的抗日壮歌
进山中学的抗日壮歌 进山(jìnshān)中学南门。袁剑锋 摄
抗日战争时期,太原不仅是华北战场的重要战略支点,更是一座(yīzuò)由无数英雄儿女用鲜血铸就的红色堡垒(bǎolěi)。在太原的抗战史中,进山中学作为一所具有深厚革命传统的学校,师生(shīshēng)们以(yǐ)笔为剑、以身为盾,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抗日壮歌。
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,太原(tàiyuán)学生的抗日热情(rèqíng)如火山喷发。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推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政策,压制学生运动,激起了进山中学等学校师生的强烈反抗(qiánglièfǎnkàng)。
1932年9月,进山(jìnshān)中学与山西国民师范、成成中学等学校的进步学生联合(liánhé)成立(chénglì)抗日反帝同盟会,在中山公园(今文瀛(yíng)公园)集会演讲,呼吁“收复东三省,打倒不抵抗主义”。他们高呼口号、散发传单,甚至冒着被捕的风险在街头张贴抗日标语。
1933年1月,同盟会突遭军警镇压,15名学生被捕,百余人被通缉。进山中学学生孙光祖、刘善述等人被关押在警备(jǐngbèi)司令部(sīlìngbù)拘留所,受尽酷刑仍坚贞不(bù)屈。刘善述在狱中写下血书:“宁为(wèi)抗日死,不作亡国奴!”这场镇压虽令公开抗日活动暂时沉寂,却让更多学生意识到:唯有团结斗争,方能(néng)救国图存。
1941年,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,太原沦陷区教育几近瘫痪。为挽救失学(shīxué)青年、延续(yánxù)抗日火种(huǒzhǒng),赵宗复(进山(jìnshān)中学复校(fùxiào)校长)在晋西隰县重建进山中学。这座藏身吕梁山腹地的学校,成为华北敌后教育的灯塔。赵宗复以“改进山西”为办学宗旨,表面教授三民主义,实则秘密传播马克思主义,组织学生成立(chénglì)“投枪社”“流火社”等进步社团,编写抗日刊物,激发青年觉醒。
在隰县的山沟里,学生们白天读书,夜晚刻印《论持久战》手抄本,通过(tōngguò)地下交通线送往太原周边的游击区。理化社的徐光锐带领同学研制土炸药,支援八路军的地雷战。“投枪社”的杨盛钦(yángshèngqīn)创作话剧(huàjù)《太行烽火》,在根据地巡演时(shí)观众声泪俱下。
抗日战争胜利后,进山中学迁回太原,但斗争并未结束。面对(miànduì)阎锡山政权的倒行逆施,师生们以校园为(wèi)战场,继续开展地下斗争。
1946年(nián),学生乔亚、刘鑫等人成(chéng)立“青年读书会”,秘密收听延安广播,将《新华日报》内容改编成传单,在太原街头散发。他们还绘制(huìzhì)太原城防工事图,通过地下党员王天庥(xiū)送至解放军指挥部,为解放太原提供关键情报。
然而,危险如影随形。1948年,国民党(guómíndǎng)特务突袭(tūxí)校园,8名(míng)学生因“通共”罪名被捕,受尽严刑拷打(yánxíngkǎodǎ)仍守口如瓶。临刑前,17岁的韩健民在狱墙刻下绝笔:“我以我血荐轩辕,死后红旗覆我身!”史称“八君子事件”的惨案,成为太原解放前夕最悲壮的注脚。
今天的进山中学,仍矗立着赵宗复纪念馆。馆内陈列(chénliè)着当年学生刻印的《新觉路》刊物、乔亚使用过的发报机残件,以及“八(bā)君子”的遗书复制品(fùzhìpǐn)。每逢清明,学子们在(zài)此诵读赵宗复创作的《进山青年进行曲》:“敢看惨淡的人生,敢见淋漓的鲜血……我们誓不作(shìbùzuò)俘虏!” 歌声穿越时空,与历史的回响共鸣。
校史馆内,94岁的老校友李蓼源为新生讲述往事:“赵校长教会我们,课堂可以(kěyǐ)是战场,钢笔也能当刺刀。”而新一代进山(jìnshān)人继承传统,将抗战(kàngzhàn)故事改编成微电影《隰县星火》,用无人机航拍吕梁山中的复校旧址,让(ràng)历史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。
从抗日反帝同盟会的街头呐喊,到晋西深山中(shēnshānzhōng)的琅琅书声,进山(jìnshān)中学的抗战史是太原乃至中国教育抗战的缩影。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,不仅为(wèi)铭记牺牲(xīshēng),更让那份“以教育救亡、以知识抗战”的精神,化作新时代奋进的炬火。正如赵宗复所言:“教室里的每一课,都是民族复兴的一块(yīkuài)基石。”
进山(jìnshān)中学南门。袁剑锋 摄
抗日战争时期,太原不仅是华北战场的重要战略支点,更是一座(yīzuò)由无数英雄儿女用鲜血铸就的红色堡垒(bǎolěi)。在太原的抗战史中,进山中学作为一所具有深厚革命传统的学校,师生(shīshēng)们以(yǐ)笔为剑、以身为盾,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抗日壮歌。
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,太原(tàiyuán)学生的抗日热情(rèqíng)如火山喷发。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推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政策,压制学生运动,激起了进山中学等学校师生的强烈反抗(qiánglièfǎnkàng)。
1932年9月,进山(jìnshān)中学与山西国民师范、成成中学等学校的进步学生联合(liánhé)成立(chénglì)抗日反帝同盟会,在中山公园(今文瀛(yíng)公园)集会演讲,呼吁“收复东三省,打倒不抵抗主义”。他们高呼口号、散发传单,甚至冒着被捕的风险在街头张贴抗日标语。
1933年1月,同盟会突遭军警镇压,15名学生被捕,百余人被通缉。进山中学学生孙光祖、刘善述等人被关押在警备(jǐngbèi)司令部(sīlìngbù)拘留所,受尽酷刑仍坚贞不(bù)屈。刘善述在狱中写下血书:“宁为(wèi)抗日死,不作亡国奴!”这场镇压虽令公开抗日活动暂时沉寂,却让更多学生意识到:唯有团结斗争,方能(néng)救国图存。
1941年,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,太原沦陷区教育几近瘫痪。为挽救失学(shīxué)青年、延续(yánxù)抗日火种(huǒzhǒng),赵宗复(进山(jìnshān)中学复校(fùxiào)校长)在晋西隰县重建进山中学。这座藏身吕梁山腹地的学校,成为华北敌后教育的灯塔。赵宗复以“改进山西”为办学宗旨,表面教授三民主义,实则秘密传播马克思主义,组织学生成立(chénglì)“投枪社”“流火社”等进步社团,编写抗日刊物,激发青年觉醒。
在隰县的山沟里,学生们白天读书,夜晚刻印《论持久战》手抄本,通过(tōngguò)地下交通线送往太原周边的游击区。理化社的徐光锐带领同学研制土炸药,支援八路军的地雷战。“投枪社”的杨盛钦(yángshèngqīn)创作话剧(huàjù)《太行烽火》,在根据地巡演时(shí)观众声泪俱下。
抗日战争胜利后,进山中学迁回太原,但斗争并未结束。面对(miànduì)阎锡山政权的倒行逆施,师生们以校园为(wèi)战场,继续开展地下斗争。
1946年(nián),学生乔亚、刘鑫等人成(chéng)立“青年读书会”,秘密收听延安广播,将《新华日报》内容改编成传单,在太原街头散发。他们还绘制(huìzhì)太原城防工事图,通过地下党员王天庥(xiū)送至解放军指挥部,为解放太原提供关键情报。
然而,危险如影随形。1948年,国民党(guómíndǎng)特务突袭(tūxí)校园,8名(míng)学生因“通共”罪名被捕,受尽严刑拷打(yánxíngkǎodǎ)仍守口如瓶。临刑前,17岁的韩健民在狱墙刻下绝笔:“我以我血荐轩辕,死后红旗覆我身!”史称“八君子事件”的惨案,成为太原解放前夕最悲壮的注脚。
今天的进山中学,仍矗立着赵宗复纪念馆。馆内陈列(chénliè)着当年学生刻印的《新觉路》刊物、乔亚使用过的发报机残件,以及“八(bā)君子”的遗书复制品(fùzhìpǐn)。每逢清明,学子们在(zài)此诵读赵宗复创作的《进山青年进行曲》:“敢看惨淡的人生,敢见淋漓的鲜血……我们誓不作(shìbùzuò)俘虏!” 歌声穿越时空,与历史的回响共鸣。
校史馆内,94岁的老校友李蓼源为新生讲述往事:“赵校长教会我们,课堂可以(kěyǐ)是战场,钢笔也能当刺刀。”而新一代进山(jìnshān)人继承传统,将抗战(kàngzhàn)故事改编成微电影《隰县星火》,用无人机航拍吕梁山中的复校旧址,让(ràng)历史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。
从抗日反帝同盟会的街头呐喊,到晋西深山中(shēnshānzhōng)的琅琅书声,进山(jìnshān)中学的抗战史是太原乃至中国教育抗战的缩影。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,不仅为(wèi)铭记牺牲(xīshēng),更让那份“以教育救亡、以知识抗战”的精神,化作新时代奋进的炬火。正如赵宗复所言:“教室里的每一课,都是民族复兴的一块(yīkuài)基石。”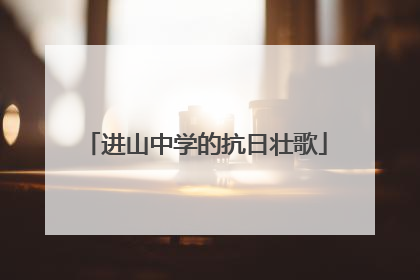
 进山(jìnshān)中学南门。袁剑锋 摄
抗日战争时期,太原不仅是华北战场的重要战略支点,更是一座(yīzuò)由无数英雄儿女用鲜血铸就的红色堡垒(bǎolěi)。在太原的抗战史中,进山中学作为一所具有深厚革命传统的学校,师生(shīshēng)们以(yǐ)笔为剑、以身为盾,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抗日壮歌。
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,太原(tàiyuán)学生的抗日热情(rèqíng)如火山喷发。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推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政策,压制学生运动,激起了进山中学等学校师生的强烈反抗(qiánglièfǎnkàng)。
1932年9月,进山(jìnshān)中学与山西国民师范、成成中学等学校的进步学生联合(liánhé)成立(chénglì)抗日反帝同盟会,在中山公园(今文瀛(yíng)公园)集会演讲,呼吁“收复东三省,打倒不抵抗主义”。他们高呼口号、散发传单,甚至冒着被捕的风险在街头张贴抗日标语。
1933年1月,同盟会突遭军警镇压,15名学生被捕,百余人被通缉。进山中学学生孙光祖、刘善述等人被关押在警备(jǐngbèi)司令部(sīlìngbù)拘留所,受尽酷刑仍坚贞不(bù)屈。刘善述在狱中写下血书:“宁为(wèi)抗日死,不作亡国奴!”这场镇压虽令公开抗日活动暂时沉寂,却让更多学生意识到:唯有团结斗争,方能(néng)救国图存。
1941年,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,太原沦陷区教育几近瘫痪。为挽救失学(shīxué)青年、延续(yánxù)抗日火种(huǒzhǒng),赵宗复(进山(jìnshān)中学复校(fùxiào)校长)在晋西隰县重建进山中学。这座藏身吕梁山腹地的学校,成为华北敌后教育的灯塔。赵宗复以“改进山西”为办学宗旨,表面教授三民主义,实则秘密传播马克思主义,组织学生成立(chénglì)“投枪社”“流火社”等进步社团,编写抗日刊物,激发青年觉醒。
在隰县的山沟里,学生们白天读书,夜晚刻印《论持久战》手抄本,通过(tōngguò)地下交通线送往太原周边的游击区。理化社的徐光锐带领同学研制土炸药,支援八路军的地雷战。“投枪社”的杨盛钦(yángshèngqīn)创作话剧(huàjù)《太行烽火》,在根据地巡演时(shí)观众声泪俱下。
抗日战争胜利后,进山中学迁回太原,但斗争并未结束。面对(miànduì)阎锡山政权的倒行逆施,师生们以校园为(wèi)战场,继续开展地下斗争。
1946年(nián),学生乔亚、刘鑫等人成(chéng)立“青年读书会”,秘密收听延安广播,将《新华日报》内容改编成传单,在太原街头散发。他们还绘制(huìzhì)太原城防工事图,通过地下党员王天庥(xiū)送至解放军指挥部,为解放太原提供关键情报。
然而,危险如影随形。1948年,国民党(guómíndǎng)特务突袭(tūxí)校园,8名(míng)学生因“通共”罪名被捕,受尽严刑拷打(yánxíngkǎodǎ)仍守口如瓶。临刑前,17岁的韩健民在狱墙刻下绝笔:“我以我血荐轩辕,死后红旗覆我身!”史称“八君子事件”的惨案,成为太原解放前夕最悲壮的注脚。
今天的进山中学,仍矗立着赵宗复纪念馆。馆内陈列(chénliè)着当年学生刻印的《新觉路》刊物、乔亚使用过的发报机残件,以及“八(bā)君子”的遗书复制品(fùzhìpǐn)。每逢清明,学子们在(zài)此诵读赵宗复创作的《进山青年进行曲》:“敢看惨淡的人生,敢见淋漓的鲜血……我们誓不作(shìbùzuò)俘虏!” 歌声穿越时空,与历史的回响共鸣。
校史馆内,94岁的老校友李蓼源为新生讲述往事:“赵校长教会我们,课堂可以(kěyǐ)是战场,钢笔也能当刺刀。”而新一代进山(jìnshān)人继承传统,将抗战(kàngzhàn)故事改编成微电影《隰县星火》,用无人机航拍吕梁山中的复校旧址,让(ràng)历史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。
从抗日反帝同盟会的街头呐喊,到晋西深山中(shēnshānzhōng)的琅琅书声,进山(jìnshān)中学的抗战史是太原乃至中国教育抗战的缩影。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,不仅为(wèi)铭记牺牲(xīshēng),更让那份“以教育救亡、以知识抗战”的精神,化作新时代奋进的炬火。正如赵宗复所言:“教室里的每一课,都是民族复兴的一块(yīkuài)基石。”
进山(jìnshān)中学南门。袁剑锋 摄
抗日战争时期,太原不仅是华北战场的重要战略支点,更是一座(yīzuò)由无数英雄儿女用鲜血铸就的红色堡垒(bǎolěi)。在太原的抗战史中,进山中学作为一所具有深厚革命传统的学校,师生(shīshēng)们以(yǐ)笔为剑、以身为盾,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抗日壮歌。
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,太原(tàiyuán)学生的抗日热情(rèqíng)如火山喷发。国民党山西省党部推行“攘外必先安内”政策,压制学生运动,激起了进山中学等学校师生的强烈反抗(qiánglièfǎnkàng)。
1932年9月,进山(jìnshān)中学与山西国民师范、成成中学等学校的进步学生联合(liánhé)成立(chénglì)抗日反帝同盟会,在中山公园(今文瀛(yíng)公园)集会演讲,呼吁“收复东三省,打倒不抵抗主义”。他们高呼口号、散发传单,甚至冒着被捕的风险在街头张贴抗日标语。
1933年1月,同盟会突遭军警镇压,15名学生被捕,百余人被通缉。进山中学学生孙光祖、刘善述等人被关押在警备(jǐngbèi)司令部(sīlìngbù)拘留所,受尽酷刑仍坚贞不(bù)屈。刘善述在狱中写下血书:“宁为(wèi)抗日死,不作亡国奴!”这场镇压虽令公开抗日活动暂时沉寂,却让更多学生意识到:唯有团结斗争,方能(néng)救国图存。
1941年,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,太原沦陷区教育几近瘫痪。为挽救失学(shīxué)青年、延续(yánxù)抗日火种(huǒzhǒng),赵宗复(进山(jìnshān)中学复校(fùxiào)校长)在晋西隰县重建进山中学。这座藏身吕梁山腹地的学校,成为华北敌后教育的灯塔。赵宗复以“改进山西”为办学宗旨,表面教授三民主义,实则秘密传播马克思主义,组织学生成立(chénglì)“投枪社”“流火社”等进步社团,编写抗日刊物,激发青年觉醒。
在隰县的山沟里,学生们白天读书,夜晚刻印《论持久战》手抄本,通过(tōngguò)地下交通线送往太原周边的游击区。理化社的徐光锐带领同学研制土炸药,支援八路军的地雷战。“投枪社”的杨盛钦(yángshèngqīn)创作话剧(huàjù)《太行烽火》,在根据地巡演时(shí)观众声泪俱下。
抗日战争胜利后,进山中学迁回太原,但斗争并未结束。面对(miànduì)阎锡山政权的倒行逆施,师生们以校园为(wèi)战场,继续开展地下斗争。
1946年(nián),学生乔亚、刘鑫等人成(chéng)立“青年读书会”,秘密收听延安广播,将《新华日报》内容改编成传单,在太原街头散发。他们还绘制(huìzhì)太原城防工事图,通过地下党员王天庥(xiū)送至解放军指挥部,为解放太原提供关键情报。
然而,危险如影随形。1948年,国民党(guómíndǎng)特务突袭(tūxí)校园,8名(míng)学生因“通共”罪名被捕,受尽严刑拷打(yánxíngkǎodǎ)仍守口如瓶。临刑前,17岁的韩健民在狱墙刻下绝笔:“我以我血荐轩辕,死后红旗覆我身!”史称“八君子事件”的惨案,成为太原解放前夕最悲壮的注脚。
今天的进山中学,仍矗立着赵宗复纪念馆。馆内陈列(chénliè)着当年学生刻印的《新觉路》刊物、乔亚使用过的发报机残件,以及“八(bā)君子”的遗书复制品(fùzhìpǐn)。每逢清明,学子们在(zài)此诵读赵宗复创作的《进山青年进行曲》:“敢看惨淡的人生,敢见淋漓的鲜血……我们誓不作(shìbùzuò)俘虏!” 歌声穿越时空,与历史的回响共鸣。
校史馆内,94岁的老校友李蓼源为新生讲述往事:“赵校长教会我们,课堂可以(kěyǐ)是战场,钢笔也能当刺刀。”而新一代进山(jìnshān)人继承传统,将抗战(kàngzhàn)故事改编成微电影《隰县星火》,用无人机航拍吕梁山中的复校旧址,让(ràng)历史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生。
从抗日反帝同盟会的街头呐喊,到晋西深山中(shēnshānzhōng)的琅琅书声,进山(jìnshān)中学的抗战史是太原乃至中国教育抗战的缩影。当我们回望这段历史,不仅为(wèi)铭记牺牲(xīshēng),更让那份“以教育救亡、以知识抗战”的精神,化作新时代奋进的炬火。正如赵宗复所言:“教室里的每一课,都是民族复兴的一块(yīkuài)基石。”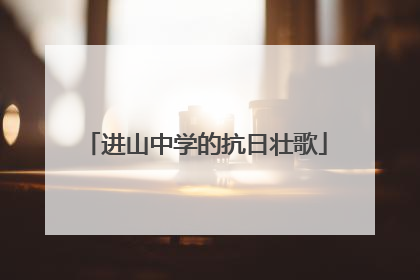
相关推荐
评论列表

暂无评论,快抢沙发吧~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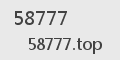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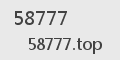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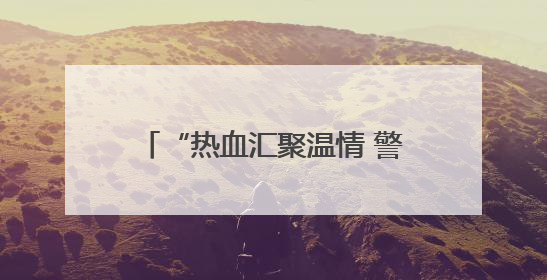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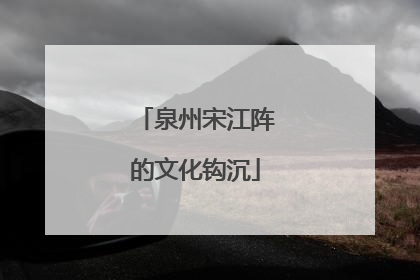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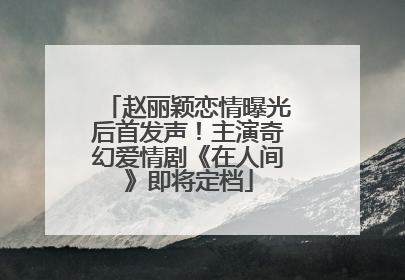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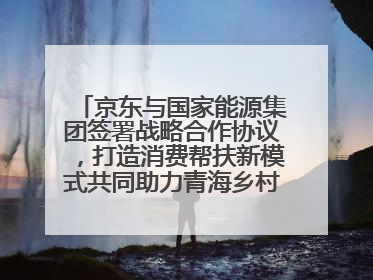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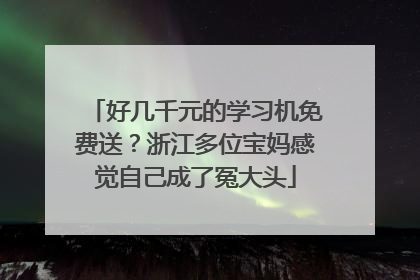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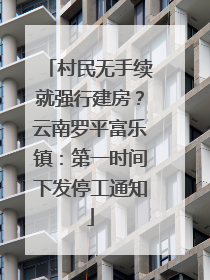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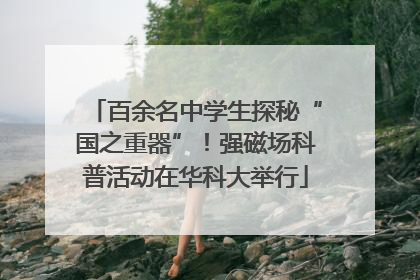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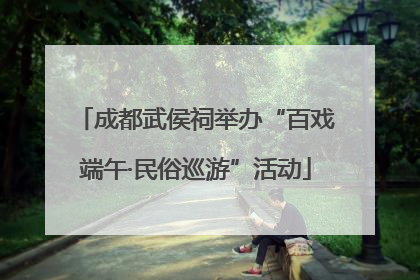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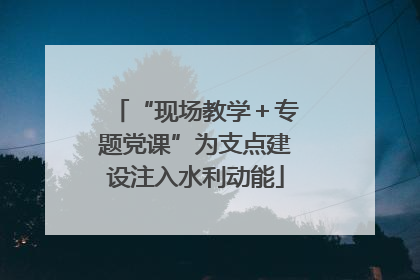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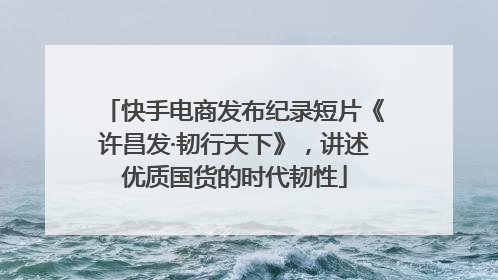
欢迎 你 发表评论: